农商行风险这轮怎么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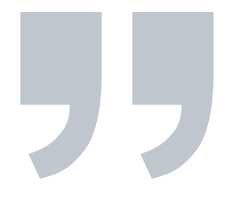
正文:
近期部分地区村镇银行等基层金融乱象引起业内广泛关注。风起青萍之末,基层经营乱象折射了区域金融机构经营问题,破坏了当地基层信用生态,甚至引起投资者对地区金融风险的担忧。本文以区域农商行为视角,分析相关机构的风险状况。
一、农商行尾部风险明显
按照中银协2021年底统计,我国已改制组建农村商业银行超过已1500家,农信社超过600家,总资产规模超过45万亿元,其中90%以上贷款投向县域农户和小微企业。农村金融机构覆盖网点多,客户下沉程度高,是我国服务普惠的“毛细血管网”,振兴乡村发展的“主力军”。
我国部分区域银行在公司治理和流动性层面在2017年“去杠杆”后持风险暴露。2019年以来,包括包商银行、锦州银行被接管处置等风险事件陆续出现。相关机构出现风险一方面在于公司治理,即部分机构民营股东借助控制权安排挪用、掏空旗下金融机构资源;另一方面在于流动性冲击,相关中小银行在负债端进行激进扩张,在资产端通过投资类资产下沉信用层级,实现跨区域投放资产,但自身流动性管理资能力不足,长期限资产持有多,资产变现难度大,同业负债占比过大,一旦面临政策或市场的调整或突发状况,相关银行面临资产负债错配带来的压力。
同时,农村金融相比其他金融机构体现出差异化的风险特征。尤其是农地金融化过程涉及民生基础保障和农民根本权益,客户资质普遍偏弱,抵押物难可靠处置等,具体体现在如政策风险和法律风险,如农业生产下的信用违约风险,如农业土地处置风险等。按照央行发布的2021年四季度央行金融机构评级结果,通过同业机构比较,农村金融机构(包括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信社)和村镇银行风险最高,其中高风险机构数量分别为186家和103家,资产分别占本类型机构的5%、7%。
二、引入兴业多维度评价体系
我们引入兴业研究针对商业银行的风险分析框架做更进一步讨论。根据下图,我们研究框架在分析传统分析大行宏观环境、流动性环境、监管政策等因素基础上重点增加了对区域经济、公司治理、资产负债结构等维度。后者更能解释不同区域地方金融机构的差异特征。
2.1 维度一:区域发展
我们观察到经历过2017年“去杠杆”后农商行资产规模与本地经济状况相关性显著增强。2016年之前,区域银行可以通过同业业务创新拓展资产渠道,脱实向虚后,资产增速可以显著高于本地经济增长;2017年开始,随着“三三四”检查与监管政策趋严,本地银行资产端逐步从对外投资回归本地信贷,与本地经济状况的相关性显著增强。

下图展示了不同区域银行的资产增速。整体看,北上广深、长三角、珠三角区域等保持了稳定增长,同时华北和中原地区、西南地区整体资产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东北地区从2016年前的高增速有显著下滑,直到2021年才有所恢复。当然,我们主要基于头部农商行样本,实际上随着层级下沉细分,不同地域的金融机构又会有差异化的特点。
2.2 维度二:公司治理
相对城商行,农商行体现出股权比例更分散的特征。由于区域农商行多来自于本地农信社改制,早年因资本金不足引入了较多本地资本,这导致了农商行股东结构复杂,股权分散的历史遗留问题。从新兴市场公司治理角度,很难说股权结构集中还是分散好,集中有利于大股东“援助”旗下公司,尤其对于持续资本金“饥渴”的金融机构,过于分散的股权结构可能不利于资本补充;而股权集中也会导致大股东通过关联交易“掏空”旗下公司的可能性,近年来出现风险的包商银行、锦州银行均体现出民营股东“造系”、一股独大等问题。在近期河南区域村镇银行风险事件中,2022年5月20日银保监通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该事件还涉及其他主体和其他复杂的交易结构,如这几家村镇银行的大股东河南某集团利用第三方平台或通过资金掮客吸收公众资金,涉嫌违法犯罪。整体上,结合区域实际背景,我们认为股东较集中,国有股东和民营股东能有一定制衡的区域银行风险状况相对可控。
2.3 维度三:经营情况
2022年商业银行经营既受困于疫情冲击反复,也受益于持续的稳增长策略。开年以来,一方面经济稳增长目标未变,基建和地产融资边际有所放开,除政府专项债外,包括信托融资等多种融资途径有一定恢复,预计后续财政政策端将更加发力。但同时,我们也要关注到开年以来,俄罗斯乌克兰冲突导致商品持续大涨,影响产业链利润分配,中下游企业盈利受损,信用环境恶化;本轮疫情对经济冲击为常态化防控以来最大,服务业景气度下滑,供应链摩擦明显,居民消费不振,加杠杆意愿偏弱。
近期商业银行经营在“量”(即信贷规模增长)和“价”(即净息差水平)的逻辑并不一致。其中,量增受益于财政对冲政策加码,而价弱拖累于信贷结构。从2022年一季报看,机构资产规模增速回升,国有行营收增速优于股份行,判断这与财政政策发力为主,国有大行项目储备更多有关;信贷结构上,一季度投放以企金短期贷款和票据为主(占七成),而企业中长期贷款和居民贷款偏弱,整体上低收益资产占比上升。
考虑到区域银行尤其是农商行缺乏大政府基建项目储备,整体客户结构较下沉,预计受疫情冲击影响强度要大于国有大行。进一步从长窗口信贷质量(不良贷款率和关注类贷款率)视角分析,2016年以来各区域资产质量整体稳中略有改善,而东北地区银行仍在高位徘徊,华北和环渤海地区从高点有所回落。同时,相对于城商行,农商行普遍选择加大了拨备计提,拨备覆盖率提升至300%以上较稳健的中枢水平。
2.4 维度四:公司治理变化
对区域金融机构,风险和机会也在赛跑,这体现在区域银行兼并收购等事件催化。2020年以来,已经超过20多家中小银行完成或正在经历合并重组。整合区域内金融资源,提升抗金融风险能力这是化解区域银行经营风险的典型举措,近期河南(中原银行主导)、辽宁(新设辽沈银行)、山西(新设山西银行)、四川(新设四川银行)等省份出现城商行系统性整合机会,而浙江联社整体改制成联合农商行,未来我国各省均将涌现一批资产规模过万亿元的“超级地方银行”,同业生态又有新的变化。整体看,区域银行间的整合增厚了机构资本实力,减轻了同业机构的金融风险。
三、总结:机构业务下沉过程亦应关注同业风险
通过引入兴业研究针对商业银行的风险分析框架,本文在宏观经济、流动性和监管环境基础上,从区域经济、公司治理、资产负债结构等维度分析区域银行发展。主要结论体现在:第一,从区域发展维度看,随着“去杠杆”推进,北上广深、长三角、珠三角区域金融机构与当地经济发展保持一致,华北地区、西南地区银行有更快增长,而东北区域银行随当地经济不振陷入了发展困局;第二,相对城商行,农商行体现出股权比例更分散的特征,考虑到农商行普遍需要持续资本补充的事实,判断股东较集中,国有股东和民营股东能有一定制衡的区域银行风险状况相对可控;第三,2022年以来,考虑到区域农商行缺乏大政府基建项目储备,整体客户结构较下沉,预计受疫情冲击影响强度要大于国有大行;第四,区域农商行风险和机会也在赛跑,这体现在区域银行兼并收购等事件催化,尤其是联社改制可能推动形成一批大体量的农商行,进而影响本地农信金融生态。
同业业务下沉之际,亦应关注对手方风险。尤其近年来,较多机构持续丰富同业业务内涵。除传统投资业务外,通过财富理财代销、数字化体系建设等方式参与新型同业业务,业务范畴从传统城商行、农商行下沉到农信社、村镇银行等基层机构组织。表面看相关业务不消耗或低消耗资本,但实际上交易对手风险也会影响相关业务正常履行。
通过近期基层金融活动乱象事实,基层同业机构的风险应予以重点识别和防范。按照拨备监管政策导向,要求将包括同业资产在内的非信贷类资产纳入拨备计提。这符合银行信用资产多元化的发展方向,但对非信贷类资产潜在风险估计值如何科学计算仍较为模糊,作为应对商业银行普遍会多计提信贷类资产减值准备,少提非信贷类资产减值准备。本文的分析框架可以为解决相关问题提供一定思路。
**注:农商行样本选择具体参考《去杠杆后的中国区域银行—透过财报看银行经营系列之四》
转载声明
转载申请请联系market-service@cib.com.cn邮箱,我们尽快给予回复。本报告相关内容未经我司书面许可,不得进行引用或转载,否则我司保留追诉权利。
服务支持人员
-
李璐琳021-2285275113262986013liliulin@cib.com.cn
-
汤灏021-2285263013501713255tanghao@cib.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