谋而后动,静待时机—2021年利率市场展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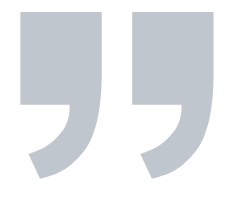
2020年,在疫情冲击之下,债市全年呈V型走势。到第四季度,10年国债收益率已一度有效突破3.3%,超过了2019年第四季度疫情爆发前的高点。那么,如何看待2021年的利率市场走势?本轮利率的高点何时到来?
一、宏观经济形势
1、经济增长
回顾2020年,得益于强有力的疫情防控措施和宏观政策的逆周期扩张,中国经济率先从疫情中复苏。到2020年第四季度,经济已经出现了局部过热的迹象。
第一,2020年10月工业增加值与服务业同比增速均超过疫情前的水平。2020年10月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9%,高于2019年第四季度的5.9%;2020年10月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7.4%,高于2019年第四季度的6.7%。同时,2020年11月的制造业和服务业PMI均显示经济景气度在进一步上升。
第二,工业品领域的通胀苗头开始显现。2020年第三季度以来铜、铁矿石、焦炭、玻璃等工业品价格显著攀升,均创下或接近201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2020年10月工业企业利润当月同比增长28.2%,达到2012年3月有数据以来的最高水平。
第三,融资需求旺盛,贷款额度趋紧。2020年6月至11月,新增企业中长期贷款保持在4000亿以上,而且6月至10月新增表内票据融资持续为负,反映出贷款额度趋紧。央行发布的贷款需求指数也处于2014年以来的较高水平。
展望2021年,经济复苏的态势还将继续。与2019年第四季度相比,2020年第三季度农林牧渔、制造业、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和信息服务业的GDP同比增速已经更高,但批发零售业、交运仓储业、住宿餐饮业、租赁商服和其他行业的GDP同比增速依然偏低。上述行业在2021年将有不同的表现。
第一,疫情的减轻和疫苗的推广将使批发零售等服务业加速恢复。从上图中不难看出,GDP同比还未恢复至疫情前水平的行业主要是涉及人与人接触的服务业,而疫情是影响上述行业复苏进度的主要因素。2020年第四季度以来,新冠疫苗研发捷报频传。多款疫苗临床Ⅲ期的有效性达到70%以上。依据国内疫苗研发单位披露的数据,如果疫苗研发进展顺利,到2021年国内新冠疫苗产能有望超过10亿剂,足以支持国内大范围接种疫苗。随着新冠疫苗普及度的提高,服务业的增长潜力将得到释放。
第二,逆周期政策的退出将削弱房地产业、建筑业和金融业增长的动力。随着经济逐渐走出疫情的阴影,逆周期政策也将有序退出,2021年的货币与财政政策力度都将低于2020年。
一方面,房地产业和金融业的增长都与信用周期密切相关。2020年10月央行行长易纲在金融街论坛上表示:“货币政策要把握好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平衡,既不让市场缺钱,也不让市场的钱溢出来,保持货币供应与反映潜在产出的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基本匹配。”同样在10月,易纲行长在《中国金融》杂志发表的文章中指出:“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速,从2016年末的11%左右降至2019年末的8.7%,与反映潜在产出的名义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基本匹配。”这可能意味着2021年的M2与社融增速将向2019年末的水平靠拢。在货币与信用增长放缓的背景下,金融业与房地产业的GDP增速也将出现回落。
另一方面,建筑业深受房地产投资和基建投资的影响,而房地产投资和基建投资的增长往往伴随着居民部门和政府部门杠杆率的抬升。因此,数据显示实体部门杠杆率与建筑业GDP同比有关。2020年10月央行行长易纲曾提到:“明年GDP增速回升后,宏观杠杆率将会更稳一些。”在实体部门杠杆率更为稳定的背景下,建筑业GDP的增长速度可能出现放缓。
不过,房地产业与建筑业的下行压力可能在2021年下半年显现。宏观杠杆率的变化对房地产业GDP同比有一定的领先性,而地方债发行的同比变化对建筑业GDP同比有一定的领先性。由此来看,信用扩张的滞后影响有望延续到2021年上半年。
第三,全球经济复苏有望使制造业维持较高的景气度。IMF、世界银行和OECD预测2021年全球GDP增速将上升至4.0%至5.5%之间。海外需求的回升将使出口继续以较快的速度增长,制造业的高景气在2021年上半年有望延续。不过,进入2021年下半年后,房地产和基建投资的放缓可能对制造业生产形成拖累。
2、物价
随着经济由复苏转向局部过热,物价上涨的压力将逐渐显现。自2020年3月我国逐渐复工复产以来,经济景气先行指数显著上升,预示着2021年GDP平减指数的同比增长有望加快。然而,物价上涨的压力将更多地体现在工业品领域而非消费品领域。
从CPI来看,2019年以来我国猪价波动较大,成为影响CPI走势的主要因素。然而,在猪价大幅上涨、养殖利润提高的激励下,生猪产能已经开始恢复。猪肉供应缺口将收窄,进而带来猪价下降的压力。同时,由于2020年猪肉价格总体偏高,2021年CPI翘尾的均值大约在-0.4%左右,较2020年的2.2%低2.6个百分点。总体来看,2021年CPI同比将显著下降。
从PPI来看,M1是PPI重要的领先指标。这是由于企业现金流的改善能够增强其采购原材料的意愿和能力。2020年11月M1同比上升至10.0%,创下2018年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由此来看,未来PPI同比降幅将进一步收窄。PPI同比有望在2021年第一季度转正。
3、货币政策
随着经济逐渐走出疫情的影响,货币政策的重心将从稳增长转向防风险。为了实现防风险,货币当局可能在量、价两方面均有所收紧。
从利率来看,11月18日央行金融研究所所长周诚君表示:“总体而言,我国目前市场利率水平低于自然利率均衡水平。市场利率水平低于均衡自然利率水平,会带来某种程度的扭曲,导致资源分配到一些低效率领域,会产生一定程度的道德风险。”[1]考虑到2021年经济增长将回到潜在水平以上,将市场利率维持在低于自然利率的水平可能引发风险。因此,央行可能通过公开市场操作抬升DR007中枢,甚至调高7天逆回购利率。
另外,尽管2021年CPI和PPI同比可能处于较低水平,但央行货币政策操作中对于经济活动和通胀的考察或许不仅限于上述指标。11月27日,周小川在《拓展通货膨胀的概念与度量》[2]一文中指出:“传统的通胀度量会面临几个方面的不足和挑战:较少包含资产价格会带来失真,特别是长周期比较的失真;以什么收入作为计算通胀的支出篮子;劳动付出的度量如何影响通胀的感知;基准、可比性(comparability)和参照系。”历史经验表明,工业企业利润累计同比增速是7天逆回购利率的领先指标。在工业企业利润累计同比转正后一段时间,可能出现逆回购利率上调的情况。2012年10月至2013年,虽然工业企业利润累计同比已经实现正增长,但是PPI同比依然为负,而央行依然择机收紧了货币政策。而2020年10月工业企业利润累计同比已经转正,这意味着7天逆回购利率上调的风险已经开始出现。
从量来看,为了稳定宏观杠杆率,2021年社融与M2同比增速将双双下降。观察2013年以来的情况,我国的贷款余额同比增速与名义GDP增速基本上呈现反向变动,反映出货币政策随着经济基本面的变化进行逆周期调控。2021年名义GDP同比增速将高于2020年,这或促使2021年贷款增速下降。
二、利率债供给和需求分析
1、利率债供给规模测算
预计2021年随着经济逐步走出疫情影响,财政收入增速回升,财政支出压力减轻,赤字规模或将有所减少,赤字率较2020年下降。2020年,财政赤字率首次提高到3.6%以上,财政赤字规模合计3.76万亿元,其中,中央财政赤字规模为2.78万亿元,地方财政赤字规模为0.98万亿元,另安排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地方政府专项债额度为3.75万亿元。根据兴业研究宏观团队的预测,2021年预算赤字率约为2.8%左右,而当年名义GDP增速约为11.2%,由此2021年赤字规模将为3.17万亿元左右,会相比2020年减少约0.59万亿元。
预计2021年新增国债规模2.1万亿元。根据2016年至2019年的中央和地方财政赤字规模分配比重,预计2021年中央和地方财政赤字规模分别为2.1万亿元和1.1万亿元。预计2021年特别国债大概率会退出,2021年新增国债规模约为2.1万亿元,加上到期规模约3.4万亿元[3],总供给预计约为5.5万亿元。
预计2021年新增地方政府一般债券1.1万亿元,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2.5万亿元。地方政府债方面,估算其发行量时通常需要考虑到3个方面,一是新增债务规模,二是债务置换情况,三是再融资规模。新增债券方面,根据前文的估算,预计2021年地方财政赤字规模约为1.1万亿元,对应于地方政府一般债新增额度1.1万亿元。从历年数据来看,财政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主要表现为广义赤字率与GDP增速明显的负相关关系,预计2021年广义赤字率由2020年的8.3%明显下降至5.0%,新增专项债额度由2020年的3.75万亿元下降至2.5万亿元。置换债券方面[4],截止2020年10月,剩余待置换存量政府债务(非债券形式)为1915亿元。其发行时点较为随机,加之绝对量较小,因此这部分债券在进行总量估算时可忽略不计。再融资债券方面,当年到期的债券会产生相应的新发债券额度,从历史经验看,约85%左右的到期债券会进行再融资。2021年地方政府债券到期规模约2.7万亿元[5],据此推算,预计2021年再融资债券发行规模约2.3万亿元。综合来看,预计2021年地方政府债总供给量约为6万亿元。
预计2021年地方债发行期限将较2020年缩短。地方债发行期限结构上,财政部数据显示,2020年1-10月地方政府债券平均发行期限14.89年,比2019年同期延长4.77年。其中,一般债券15.00年,专项债券14.84年。10年期及以上债券发行4.7万亿元,占比77.40%,比 2019年的 46.83%高30.57个百分点。相较于过去,2019年后地方政府债加权平均发行期限明显拉长,由2019年前的6年左右拉长至2019年的约10年,2020年更进一步拉长至逾15年,未来预计长期限地方债供给规模或有所降低。根据财政部2020年11月4日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做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中优化地方债期限结构的要求,“年度新增一般债券平均发行期限应当控制在10年以下(含10年),10年以上(不含10年)新增一般债券发行规模应当控制在当年新增一般债券发行总额的30%以下(含30%),再融资一般债券期限应当控制在10年以下(含10年)” [6]。
预计2021年政金债发行规模为5万亿元,净融资额为2万亿元。历史数据显示,政金债的余额增速自2013年后基本稳定于8%至12%之间,均值约为10%,与社融和M2增速的趋势保持一致。2020年,受疫情影响,政策性银行加大了对实体经济、特定领域的资金支持,截至2020年11月末,政金债的发行量为5.1万亿元,净融资额为2.4万亿元;政金债余额增速已超过12%,全年政金债余额增速或达13%左右。预计2021年政金债发行量和余额增速将回落至常态区间。假设2021年政金债余额增速为10%,同时考虑到2021年政金债的到期量为近3万亿元,则2021年政金债的净融资额为2万亿元左右,总发行量近5万亿元。
综上,预计2021年利率债供给较2020年回落,预计国债的发行规模为5.5万亿元,其中新增国债2.1万亿元;地方政府债的发行规模6万亿元,其中新增地方政府一般债券1.1万亿元,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2.5万亿元;政金债发行规模5万亿元,净融资额2万亿元。
2、债券需求分析
(1)商业银行
商业银行资产增速放缓,全国性银行利率债配置更为均衡,城商行、农商行资本压力和贷款占比指标对债券配置空间形成制约。随着信用扩张速度的放缓,预计2021年商业银行资产增速较2020年整体回落。对于全国性银行而言,随着2021年地方债供给压力缓解,预计全国性银行对国债、政金债等其他利率债品种的配置将更为均衡;从债券资产在总资产中占比来看,国有大型银行的债券、贷款在总资产中占比较为稳定。对于城商行农商行而言,近年来资本持续承压,2020年受疫情冲击,资本充足率进一步下行,2021年是存量理财资产处置的最后一年,对于体量较小的银行,非标回表可能对资本产生较大压力,尽管利率债的资本占用较低,但受贷款占比等监管指标影响,中小银行债券资产的实际配置比例存在较强制约。
从债券和贷款的比价关系来看,当前贷款利率的拐点已经出现,预计后续贷款利率会继续上行。2020年9月末,一般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5.31%,较上季度环比上行5bp;考虑税收、资本占用和信用风险后,调整后的贷款收益约为2.11%,第三季度末,国债收益率相较于调整后的贷款收益高出90bp左右,较第二季度的利差走阔。当前国债收益率领先于贷款利率上行,二者间的利差走阔,预计后续贷款利率将跟随上行,但上行速度慢于国债利率,从历史经验来看,在国债利率达到高点前后,二者利差达到最大值。
商业银行存款成本较2020年持平或边际小幅提升。2020年上半年,随着市场利率下行,商业银行调降了一般性存款报价;同时,结构性存款压降,商业银行负债成本下行;存款增速也达到近年来的高点。展望2021年,随着信用扩张放缓,存款增速回落,预计2021年存款成本与2020年基本持平或边际小幅提升。
(2)广义基金
资管新规过渡期最后一年,银行理财进一步增配利率债、信用债,压降非标资产,类货基持仓结构面临调整, 定开债基和摊余债基的潜在风险需要重新审视。
银行理财的资产配置中,债券投资占比逐步上升,增配品种以信用债、NCD为主。根据银行业理财登记托管中心的统计,2019年末,银行理财的债券投资占比为59%,其中,8%为利率债,51%为商业银行债、NCD、企业债等其他债券(以下简称“其他债券”),债券投资的合计比例较上年末上升4个百分点,主要来自对于其他债券品种的增配,增配规模约为2万亿元;2017-2019年,银行理财对利率债的配置比例保持稳定,对NCD、信用债等其他债券品种的配置比例持续上升。
从银行理财对利率债的配置来看,银行理财偏好政金债,对国债、地方债的配置比例较低,主要满足流动性管理需求和类货基等产品的配置需求等。截至2020年11月末,银行理财合计持有政金债9952亿元,对国债、地方债的投资规模仅124亿元和67亿元;2020年1-11月,银行理财合计增持2000亿元左右政金债。银行理财对利率债的配置规模上升,一方面来自银行理财的流动性管理需求,根据理财新规,开放式理财应当持有不低于5%的现金及利率债,“开放式公募理财产品应当持有不低于该理财产品资产净值5%的现金或者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国债、中央银行票据和政策性金融债券”;另一方面来自类货基产品的配置需求,截至2019年末,类货基产品规模超过4万亿元,在净值型理财产品中占比41%,类货基产品是理财新增债券配置的重要资金来源,随着资管新规过渡期的结束,类货基产品也将逐步调整持仓结构(不再配置同业借款等非标资产)、缩短资产久期(不再配置二级资本债等期限较长的资产)。
2021年,随着信用扩张的放缓和非标压降的推进,后续信用风险事件的发生可能更为频繁,定开债基和摊余债基的潜在风险需要重新审视。2020年11月的煤企信用风险事件,逐步演变成全市场的流动性风险,也暴露出各类机构在流动性管理中的潜在风险。一是对于券商自营等信用债持仓占比较高、依赖信用债质押回购加杠杆的机构,当信用债质押率下降时,回购融资难度上升、融资成本上行,同时,不得不抛售利率债等高流动性资产,陷入被动加杠杆的恶性循环;二是对于货币基金和定开债基,商业银行等机构投资者在流动性紧张和信用风险上升时,可能集中赎回货币基金获得流动性,同时陆续赎回存在信用风险的定开债基,对资金利率和信用利差产生进一步压力,叠加商业银行由于大额风险暴露监管,对于债券基金的持有规模受到限制,赎回效应可能更加明显;三是对于摊余债基,由于摊余债基的封闭期较长、持有的债券品种以政金债等信用风险较低的品种为主,不属于本次集中赎回的基金类型,但商业银行的摊余债基的建仓规模过高,可能导致银行表内直接持有的利率债规模下降、押品数量不足,对银行流动性产生间接影响,此外,与商业银行持有其他公募基金的影响类似,摊余债基对资本占用、流动性指标的达标不利。当前超100家以上基金已经发行摊余债基,在每家机构最多成立2只摊余债基的规定下,未来摊余债基的规模虽有进一步扩容可能,但热度或已接近高峰。
(3)保险公司
预计2021年保费收入增速提升,保险资金进一步增配债券投资。2020年1-9月,受疫情冲击,保险公司累计保费收入增速由上年同期的13%下滑至7%,保险资金新增投资增长相应放缓;预计2021年保险公司的保费收入将逐步恢复,可供投资的资金规模进一步上升。从保险资金的大类资产配置来看,2020年1-9月,保险资金的债券资产配置比例先下降后上升,由2019年末的35%小幅下降至2020年4月的34%,此后逐步提升至2020年9月的37%;对比来看,2020年1-9月,保险资金的股票和基金配置比例在13%左右小幅波动。由于保险公司的负债期限较长,债券投资以长期持有为主,偏好超长期的国债、地方债等利率债品种,从历史数据来看,保险公司通常在利率上行周期提升债券投资的占比。当前利率上行尚未结束,预计2021年保险公司仍将进一步增加对债券资产的配置。
(4)境外机构
中美利差位于高位,预计2021年境外机构对我国境内利率债仍将保持较强的配置力度。2020年以来,境外机构对我国境内利率债保持较高的投资热情,多个月份的增持规模过千亿。展望2021年,预计美国国债收益率上行的幅度较小,中美利差仍将处于较高的水平,人民币汇率的升值尚未结束,境外机构对我国境内利率债仍将保持较强的配置力度。此外,9月25日,富时罗素公司宣布将中国国债纳入富时罗素全球政府债券指数(WGBI),预计将于2021年10月生效,正式生效后预计将带来超过1400亿美元的资金流入。
三、利率走势分析
1、债市周期分析
2020年年初至今的债市演绎出“大起大落”的行情,1至4月债市在疫情冲击下走出“快牛”,5月起随着疫情形势好转、经济进入渐进复苏、货币政策开启预调微调,债市出现V型反转,转入“熊市”。进入第四季度之后,在经济进一步复苏、资金成本上升和信用风险事件的共同影响下,10年国债收益率突破3.3%,超过了2019年第四季度疫情爆发前的高点,历史分位数已回归至25%左右。具体来看,2020年至今以10年期国债为代表的利率债收益率走势大体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即2020年1月至4月,突如其来的COVID-19疫情在海内外迅速扩散,从供给、需求和金融等多个方面重挫全球经济。央行迅速进入“应急”模式,货币政策宽松加码以托底经济并稳定金融市场。债市在宽货币带动下上演“牛陡”行情。
第二阶段,即5月至8月,随着国内疫情基本得到控制,经济活动基本恢复正常,指标读数的接力好转显示基本面复苏向好的态度不断巩固,基本面拐点确认。同时,货币政策亦开始向常态化退出,宽货币预期降温,资金利率中枢抬升,加之积极财政下债券供给放量,供需矛盾突出,5月初起利率开始以高斜率反弹,曲线形态向“熊平”转变。
第三阶段,即9月至11月,随着市场对静态资金成本和经济复苏预期已有较为充分的定价,利率上行速度降低、波动空间收窄,但绝对水平已回到了没有发生疫情的2019年同期。
从利率上行幅度和持续时间上看,本轮债熊与历史上债券熊市相比或难言到位。与历史上的熊市对比,当前10年期国债收益率的变化呈以下几个特点,一是上行斜率较高且保持稳定,5月初债市开启调整至今并未发生较为明显的反弹行情。二是上行速度与高度均较为接近同为“后危机”时代的2009年。三是当前收益率的调整幅度和持续时间仍低于历史平均水平。数据显示,2008年至今的熊市最长持续16个月,最短持续10个月,平均持续12个月左右,10年期国债收益率调整幅度最大为148bps,最小为96bps,平均达100bps以上。若按此推算,当前10年期国债收益率调整的幅度(80bps)和长度(约7个月)或仍“尚欠火候”。但相对而言,1年期及3年期国债收益率的调整幅度大于10年期国债收益率,已较为接近前几轮熊市均值。
2、宏观经济指标和债市走势分析
第一,从名义GDP同比和国债利率的关系来看,2012年之前,我国名义GDP的周期波动较为明显,名义GDP同比和国债利率中枢的走势具有较好的一致性,名义GDP与国债利率中枢的高点出现的时间一致或者领先一个季度左右;2013年和2017年的两轮熊市的利率高点,名义GDP同比和10年期国债利率的相关性减弱,长端利率的上行更多受流动性持续紧张的影响,短端利率的冲高,带动长端利率向上突破。展望2021年,受低基数的影响,名义GDP同比的高点可能在第一季度出现,若名义GDP同比增速超出市场预期,债券利率存在进一步上行压力。
第二,从社融增速和国债利率的关系来看,社融增速的高点相较于国债利率的高点领先5-14个月左右,除2008年以外,其他几轮债市周期中,社融增速对国债利率的领先均超过半年以上。本轮社融的高点出现在2020年第四季度,据此推断,国债利率的高点可能在第二季度甚至更晚出现。
随着信用扩张的放缓,信用风险事件的发生可能更为频繁,对利率产生阶段性冲击。从信用利差和债市周期的关系来看,在利率上行周期,信用利差通常走阔;本轮利率上行周期中,前期信用利差持续位于低位,11月份的煤企信用风险事件,推升了信用利差;2021年,信用风险事件的发生可能更为频繁,信用利差可能进一步上行,信用风险事件的爆发也会对利率产生阶段性的冲击。
第三,从M1和国债利率的关系来看,M1对国债利率的高点存在领先性,M1同比的高点通常领先国债利率三个季度以上。2020年11月,M1同比仍在继续上升,这可能意味着本轮利率的高点出现为时尚早。
3、债券市场交易指标的信号意义
第一,从期限利差的变化上看,目前收益率曲线平坦化,期限利差处于历史较低的水平,从历史经验来看,长端利率的高点尚未出现。目前1年期国债与10年期国债期限利差为41bps,位于历史15%分位左右;3年期国债与10年期国债期限利差为24bps,同样位于历史15%分位左右;5年期国债与10年期国债期限利差为15bps,位于历史24%分位左右。逻辑上,债市走熊(利率上行)通常伴随着货币政策的收紧和短端利率的上行。而在货币政策收紧的初期,市场对货币政策调整的预期不足,导致长端利率上升幅度小于短端利率,从而引发收益率曲线平坦化,此后随着长端利率的上升,期限利差将从低点回升。历史经验显示,2008年以来10-1年的期限利差低点到10年国债收益率高点之间可能相距6到13个月,而期限利差的低点通常在40bps以下,当前的期限利差水平仍高于过去几轮熊市的低点,但距离历史“极值”的空间已较为有限。因此,综合考量历史经验,均值回归及未来经济持续修复等因素,短端利率在央行货币政策回归稳健中性、流动性环境保持均衡的背景下虽仍有上行压力,但在当前的曲线形态下长端利率或面临更大的上行风险。而后续随着期限利差逐步从低点回升,收益率曲线再度陡峭化,熊市向牛市切换的拐点亦将逐渐显现。
第二,长期国债成交占比降至15%以下往往意味着市场对长端利率较为悲观,此时往往出现利率高点。2008年至2017年4轮熊市中,除2009年外,其他3轮熊市的尾声均出现长期国债成交占比下降至15%以下的现象。具体来看,2011年2月长期国债成交量占银行间国债成交量的比例下降至7.0%,,领先利率拐点(熊转牛)6个月;2013年9月长期国债成交量占比同样下降至14%,领先利率拐点2个月;2017年11月长期国债成交量占比下降至14%,领先利率拐点2个月。回到当下,2020年8月以来长期国债成交量占比保持在25%上方(11月为28%),虽然较上半年的30%有所下降,但仍然显示长期国债的市场情绪较好,二级市场保持着较高的活跃度。从该指标看,本轮债熊或尚未达到尾声,后续数据值得持续关注。
第三,10年期国开债隐含税率触及20%以上或有一定信号意义。隐含税率是指国开债与国债之间的利差与国开收益率之间的比值。2009年以来,10年国开债的隐含税率总体呈现出“牛市收窄,熊市走扩”的特征。相比于国债,国开债的活跃度更易受到债市牛熊周期的影响。债市走牛时,国开债相对于国债交易量增大,随之产生的流动性溢价带动二者利差收窄,隐含税率收窄;反之,在债市走熊时,隐含税率走阔。从2012年至2017年的2轮牛熊市来看,10年期国开债隐含税率触及20%以上或有一定的利率拐点信号意义。具体来看,2013年10月30日,隐含税率首次突破20%,而2012年7月至2013年11月这一轮熊市的高点就在13年11月20日,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为4.72%。2017年12月25日,隐含税率再次突破20%,而2016年8月至2018年1月这一轮熊市的高点就在18年1月18日,10年国债收益率为3.98%。另外,牛市中隐含税率同样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当隐含税率位于相对低位时往往意味着债市的震荡或调整。当前10年期国开债隐含税率处于12%左右,后续数据同样值得追踪关注。
第四,政金债换手率处于低位,可能暗示着利率高点的出现。一般而言,熊市中由于利率的上行预期,债券换手率会出现持续下降,流动性较好的政金债在这一点上会体现的更明显,其波动能够更灵敏地反映市场交易特征。数据显示,2010年至2011年、2012年至2013年、2016年至2017年3轮熊市期间,政金债换手率均出现了较为明显的下行,在利率高点出现前后换手率有可能下降至10%以下。截止11月,政金债换手率约为27%,相比第二、三季度50%以上的均值有明显下滑,折射出市场交易情绪愈发谨慎,但距离历史低位仍有一定距离。
综合上述分析,预计当前利率上行尚未结束,本轮利率的高点可能出现在2021年第二季度甚至更晚,10年期国债收益率的高点可能达到3.6%-3.7%。
注:
[1]资料来源:人民银行周诚君:现在没有多少降息空间,中国证券报,2020/11/18,https://3g.163.com/news/article/FRO1DPGN00259DLP.html(查于2020/11/20)
[2]资料来源:周小川,《拓展通货膨胀的概念与度量》,中国人民银行公众号,2020/11/27,https://mp.weixin.qq.com/s/Vb5EMf8obbPz_eUFrel--A(查于2020/12/11)
[3]截至2020年12月11日统计量。
[4]所谓置换债券,是指根据全国人大于2015年8月批准的2015年地方债务限额时的规定,“对债务余额中通过银行贷款等非政府债券方式举借的存量债务,通过三年左右的过渡期,由地方在限额内安排发行地方政府债券置换”,目前绝大部分已置换完毕。
[5]截至2020年12月11日统计量。
[6]财政部,2020年11月4日,《关于进一步做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财库〔2020〕36号,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11/11/content_5560562.htm
转载声明
转载申请请联系market-service@cib.com.cn邮箱,我们尽快给予回复。本报告相关内容未经我司书面许可,不得进行引用或转载,否则我司保留追诉权利。
服务支持人员
-
李璐琳021-2285275113262986013liliulin@cib.com.cn
-
汤灏021-2285263013501713255tanghao@cib.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