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特朗普对华贸易战的“军火库”
2017年,特朗普政府对华发起“全套”贸易救济调查,以施压中国贸易让利。表现在以下两方面:其一,从工具的选择上看,对华进行“反倾销”、“反补贴”及“337”调查等常规性调查的同时,启用“301”条款、“232”条款及“201”条款非常规贸易救济措施发起调查;其二,从发起主体看,政府部门“自主”发起调查的行为增加。
借鉴里根政府贸易执政经验,特朗普政府或在以下几个方面施压中国:第一,要求限制中国输美优势产品如光伏组件、钢铁及铝制品出口数量;第二,规定中国输美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如电子产品最低限价;第三,要求中国对美放开农业、能源、娱乐、技术、医疗、金融服务及网络等市场。
在此贸易政策高压下,我国对美出口或逆势下行。

中美经贸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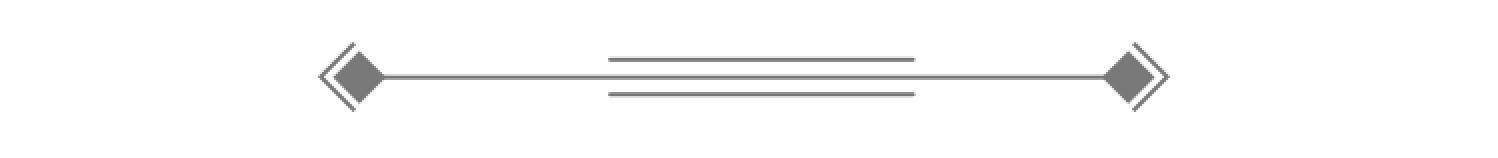
新年伊始,美国对华经贸动态不断:将中国纳入“恶名市场”名单[1],提交钢铁产品进口“232”调查结果[2],否决蚂蚁金服收购美国速汇金公司提案,搁浅华为公司与美国电信运营商电话电报公司(AT&T)合作销售手机方案[3],美国军事基地移除中国制造的监控设备[4]等,中美“贸易战”预期再度升温。据此,本文结合当前美国对华贸易救济案件及美国20世纪80年代贸易政策,分析美国对华贸易策略。
特朗普对华贸易救济工具箱全解
美国贸易救济工具主要分为多边措施和单边措施两种,其中多边措施以反倾销、反补贴为主,而单边措施则以“301”调查、“201”调查、“232”调查及“337”调查为代表,参见图表1。
工具一:反补贴、反倾销调查
反补贴、反倾销、保障措施是WTO框架下的常用贸易救济手段,也是美国限制中国产品出口的常用工具。2017年全年,美国对华发起16起贸易救济调查[5],较2016年减少3起。从案件信息动态看,美国对华贸易救济信息动态分布呈年初降、年中升、年末降态势,其中在中美“百日计划”协议达成当月,贸易救济信息动态为年内最低,参见图表2。值得关注的是,11月及12月美国对华贸易救济信息动态显著降低,这主要受特朗普访华叠加年末假日多影响。
中国连续21年作为全球遭遇反倾销、反补贴调查最多的国家,已经具备较为成熟的预警及应对措施。对此,特朗普政府或在反倾销、反补贴的威慑效应方面采取行动,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否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继而沿用“替代国价格”增加其反倾销胜诉的概率。值得注意的是,未来美国或在“替代国价格”大做文章。根据美国商务部规定,涉案企业有权建议选取“替代国价格”。但在实践中,美国商务部更多按照其确定的“替代国价格”裁定。由此,为扩大反倾销调查的打击面,美国或将选取对中国极其不利的“替代国价格”。
第二, “主动”发起调查。特朗普政府美国贸易代表官员罗伯特·莱特希泽曾为里根政府时期的贸易官员,里根政府贸易政策或在特朗普政府得以延续。2017年11月28日,美国宣布“主动”对中国输美铝产品展开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这一行为沿用了里根政府对日本半导体行业的政策,即政府部门“主动”发起调查。
工具二:“337”调查
2018年1月12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2017年恶名市场非定期回顾报告》将中国纳入其“恶名市场”名单中。长期以来,“337”调查[6]为美国攻击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矛,2017年美国对华发起25起“337”调查。具体而言:
首先,从发起主体看,共计41家企业申请对中国发起“337”调查,其中28家为美国企业、4家为日本企业,参见图表3。这表明,对华发起“337”调查的主体以美国为主,其他发达经济体为辅。进一步,根据前美国国务院中美贸易专家Anja Manuel(2017)[7]建议,美国应联合欧洲、加拿大和日本统一应对中国知识产权问题。对华发起“337”调查的企业国别分布验证了这一观点,中国将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面临着更大的国际压力。
其次,从“337”调查的涉案产品看,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为“337”调查重点对象,如电子产品为重灾区,随后依次为运输设备、医疗设备及化工产品等,参见图表4。伴随我国出口结构升级,“337”调查或成为美国威慑中国的主要工具之一。
最后,从调查结果看,“337”调查结果主要有确认侵权、不侵权、撤诉和和解四种。一旦被确认侵权,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将发布普遍排除令、有限排除令和禁止令等贸易救济措施,将涉案产品排除在美国市场外。与反倾销、反补贴相比,“337”调查具有更强的威慑效应,这导致大部分应诉企业通常采取和解方式以避免美国市场关闭。2017年“337”调查中,有5家企业和解结案,4家被撤诉,79家仍处于初裁阶段。
里根政府贸易政治倡导以市场换市场,即以关闭本国市场为威胁进而实现打开他国市场的目的。特朗普政府正沿用这一策略,“337”调查给予了其关闭本国市场较好的借口。可以预见的是,特朗普政府将联合其他发达经济体,频繁对华发起“337”调查。
工具三:“301”调查
2017年8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对华发起“301”调查。根据我们2017年8月17日发布的报告《“301”威慑的前因后果大猜想》可知,“301调查”具有威慑效应大、惩罚时间长、单边主义凸显的特点,是美国进行贸易保护威慑的“核武器”。1980-1989年期间,美国共发起53起“301”调查,显著高于70年代中后期,参见图表5。值得注意的是,在里根执政的中后期,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频繁自主发起“301”调查。无独有偶,特朗普政府沿袭里根政府风格,时隔7年再次启用“301”条款对华发起调查,表明其对中国贸易威慑正在加码。
工具四:“232”调查
2017年4月,美国商务部先后对进口钢铁产品、铝产品启动“232”调查[8],中国列为被调查国。从中国对美出口铝及其制品看,尽管当前“232”调查结果尚未落地,但其威慑效应已见成效。在中国对美出口整体平稳向好的背景下,中国输美铝及其制品快速下降,参见图表6。这或给特朗普政府以示范效应,即频繁使用“232”调查以达到减少中国对美出口,保护本国相关产业发展的目的。
进一步回顾“232”调查运用历史可知,1980年以来美国商务部共发起14例232调查案件,其中有9例发生在里根执政时期,参见图表7。特朗普政府时隔16年再次启用“232”条款,表明其贸易政治与里根政府具有极其相似之处,即频繁运用贸易救济措施以实现对他国威慑效应,进而减少进口,打开他国市场。
工具五:“201”调查
2017年5月,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应国内光伏企业Suniva申请,对全球光伏电池及组件发起保障措施调查(“201”调查)[9]。显然,中国作为全球第一大光伏产能国,是“201”调查重点对象。从中国光伏组件出口情况看,中国在美国发起“201”调查初期对美出口呈现爆发式增长,参见图表8。这折射出,光伏组件出口企业或因“制裁恐惧”提前出货。2017年9月,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做出损害裁决,认定进口产品对美国国内产业造成严重损害,将研究对进口产品采取限制措施。随后,我国对美国光伏组件出口增速也高位回落,“201”调查成效显著。
里根政府期间,美国共发起19起“201”调查,参见图表9。期间,里根政府曾对“201条款”进行修改,加入劳动条件和工资水平作为不公平贸易认定要件,进而便利“201”调查肯定性认定以限制涉案产品进口。
至此,特朗普上任一周年,不仅对华贸易政策相继频繁打出“反倾销”、“反补贴”等常规性贸易救济牌,同时也沿袭里根政府贸易政治,援引本国贸易法对华发起非常规性贸易救济调查,如“301”调查、“201”调查、“232”调查等。
特朗普对华贸易救济措施历史镜鉴
回顾2017年美国对华贸易救济措施,不难发现特朗普政府正沿袭里根政府的贸易政策。由此,我们还可进一步通过细数里根政府的贸易政策进而预判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政策。
措施一:自动出口限制
里根政府贸易政策常用手段为限制进口,即施压他国减少对美输出产品。如在里根政府贸易保护主义的威慑下,日本自动限制其汽车出口,限定日本对美国汽车出口量在168万辆,较1980年减少8%,两年后,这一限制提升至185万辆,随后将进口限制部门扩大至纺织品、服装、食糖、半导体、机床和木材等。此外,里根政府要求巴西、西班牙、韩国、日本、南非、芬兰、澳大利亚及欧盟等18个国家接受“自动限制协定”以减少钢铁进口。
在特朗普政府陆续对华打出贸易救济牌后,中国或面临部分产品自动出口限制。根据前文分析,我们认为中国在光伏组件、钢铁及铝制品面临的自动出口限制压力较大。
措施二:提高出口价格
20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亦通过施压其他经济体限定最低出口价格的方式限制进口。如1985年里根政府对日本发起“301”调查,1986年9月日本迫于制裁恐惧签署“半导体条约”,提高出口产品价格同时为美国半导体企业预留日本20%的市场份额。当前,我国同样面临“301”制裁威胁。知识产权和技术转让政策成为美国起诉中国的“抓手”,由此我国在外资准入条件及高新技术产品对美出口或面临政策调整。借鉴“337”调查行业分布经验,电子产品出口或面临价格提升的压力。
措施三:增加自美进口
增加美国产品输出主要依靠两种手段:其一,依靠政治力量打开他国市场,增加美国优势产品出口;其二,依靠政治力量要求他国增加自美进口。手段一具有较长远的经济效应而手段二则能短期见效,进而赋予美国总统执政业绩。从里根政府执政经验看,一方面施压日本汽车制造商增加进口美国制造的零部件[10];另一方面要求日本为美国半导体企业预留20%的市场份额。从特朗普对华贸易政策看,特朗普政策综合考虑短期政绩和长期经济效应两方面目标:
从长期经济效应看,2017年5月中美双方“百日计划”初步成果公报要求:中国对美放开牛肉、天然气进口市场,同时要求中国对美放开信用评级服务、电子支付服务市场。结合美国对中国贸易顺差分布项可知,特朗普政府重点在于打通其优势产品输入中国市场的渠道,参见图表10。
从短期政治业绩看, 2017年11月,中美签订价值2535亿美元的投资贸易大礼包,主要涉及能源、飞机、大豆、芯片、环保设备及汽车进口等,参见图表11。
根据Anja Manuel(2017),美国的优势产业集中在农业、能源、娱乐、技术、医疗、金融服务及网络。这也就意味着,未来美国的工作重点在于打开这些行业的中国市场。
措施四:为贸易保护措施提供更多资金支持
1981年,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通过计算美国进出口银行的收益与成本,并考虑对其增加资金支持[11]。特朗普政府对华经贸策略在于增加对华贸易救济措施以加大谈判筹码,这将加大相关部门的运营成本。据此,Anja Manuel(2017)曾建议美国增加对贸易代表办公室资金支持,以提高贸易救济调查效率。这可能意味着,在美国政府资金投入下,中美贸易摩擦将愈加频繁。
综上,伴随2017年美国对华贸易救济调查案件集中到期,美国对华贸易威慑将进一步升级。在此高压下,我国对美出口不容乐观。借鉴日本对美出口可知,在里根政府的贸易保护政治下,日本对美国出口逆势下行,参见图表12。由此,2018年中美贸易战升级或将阻碍中国出口。
注:
[1]资料来源:https://ustr.gov/
[2]资料来源:
http://news.china.com/internationalgd/10000166/20180112/31948641.html
[3]资料来源:http://www.chinanews.com/cj/2018/01-11/8421595.shtml
[4]资料来源:http://news.ifeng.com/a/20180115/55124305_0.shtml
[5]注:根据贸易救济信息网案件动态信息整理所得。
[6] “337”调查是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简称USITC)根据美国《1930年关税法》(Tariff Act of 1930)第337节(简称“337”)及相关修正案进行的调查,其目的是禁止一切不公平竞争行为或向美国出口产品中的任何不公平贸易行为。
[7]Anja Manuel《U.S.-China Trade: a Balanced Approach》
[8]根据《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章“232调查”规定,对特定产品进口是否威胁美国国家安全进行立案调查,在立案之后270天向总统提交报告,美国总统在90天内做出是否对相关产品进口采取最终措施。
[9]《1974年贸易法》第201-204节规定: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USITC)对进口至美国的产品进行全球保障措施调查,对产品进口增加是否对美国国内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或严重损害威胁作出裁定,并在120天(存在案件特别复杂的情形为150天)向总统提交报告和建议。总统根据法律授权,在收到USITC报告后140天内做出最终措施决定
[10]参见Thomas J. DiLorenzo, "ForeignManufactur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Should They Be Told to BuyAmerican?"Cato Institute Policy Analysis no. 83, February 24, 1987.
[11]资料来源:"Export-Import BankSurvives on Making Credit, Not Prof- it," Insight, January 18, 1988, pp.42-43.
特别提示:本报告内容仅对宏观经济进行分析,不包含对证券及证券相关产品的投资评级或估值分析,不属于证券报告,也不构成对投资人的建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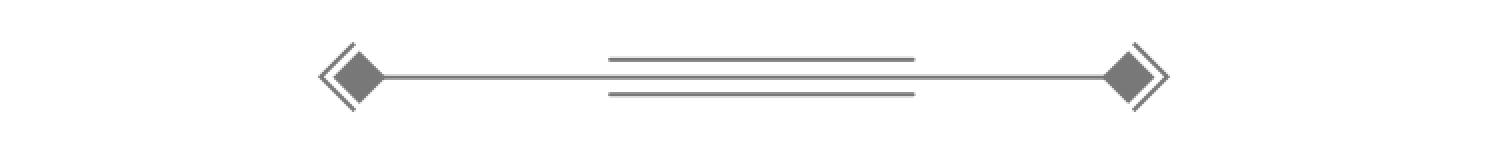
服务支持人员
-
李璐琳021-2285275113262986013liliulin@cib.com.cn
-
汤灏021-2285263013501713255tanghao@cib.com.cn




